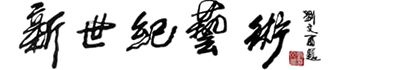
艺术分类
联系我们
Contact us
联系电话
020-81368256
工厂地址:广州市越秀区人民北路871号
当前位置:首页 > 新闻分类
诗与歌融合: 催人与命运抗争,奋发向上的音乐诗
发布时间:2023/9/11 12:10:29
诗与歌融合:催人与命运抗争,奋发向上的音乐诗
◎ 蒋德明
摘要:当今时代在进步,传播方式也在改变,诗歌需要探索更多“新”的出路。“诗+歌”的跨界融合创作表达及传播,本就是诗歌该有的样子。他大部
分作品都体现出对“生存状态”的关注与思考,而“与命运抗争”这一关乎人类生存的选题,则是诗人们孜孜不倦,一直在创作的“永恒命题”。
关键词:诗与歌,音乐诗,诗歌的出路

▲ 深圳“音乐诗人”易白
深圳特区“开拓、创新、团结、奉献”的精神,用来形容深圳诗人易白挺贴切。早年在中华诗词学会高级研修班,师从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陶先淮教授的“战士诗人”易白,系统研修完“传统诗词”理论课程与创作实践后,并没有再循规蹈矩填格律诗词,而是立足“现代诗歌创作”与“受众传播思考”另辟蹊径,研究起了音律和节奏。后来他又研究起了作曲、编曲及歌唱,通过音乐理论与经验技巧的“加持”,在十余年的创作实践中,蜕变成“音乐诗人”。
2022月11月26日,今日头条首发了易白的诗歌《公仆之病》这首诗展现量274.7万,阅读量18.7万。我看过这首诗的原稿,第一稿的标题是《我们终于确诊:集体有“病”——致抗击疫情的转业战友》。
记得那是2020年2月,新冠疫情爆发。当时曾获全国演讲比赛一等奖的退役军人邵福平,就在“喜马拉雅”平台上朗诵了这首诗,播出后反响很不错。然而,但凡诗人都有个通病,就是喜欢反复改稿;易白也是这样,即便发表很久的诗作,发现不足也要继续修改打磨;恰逢易白改稿时,老战友约他创作一首抗击疫情歌曲,后来实在想不出歌词的他,便以这首诗为心中蓝本,在机缘巧合之下,一气呵成创作了《唱给人民的信》这首歌;岂料歌曲播出后又被多家媒体转发,引爆了“1000万+”热度。
按理说,抗疫三年来,网上数以万计的抗疫诗歌、歌曲等文艺作品,如“快餐文化”发表速度之快,销声匿迹也快,属常见现象。然而,易白这首歌曲播出两年后,今日头条再次播出,展现量678.5万,播放量97.8万;该歌曲点赞、分享、转发、收藏累计2.4万人次,而这只是一个平台的数据。曾在2018年“东方风云榜·发现新声力”全国歌手大赛晋级“4强”的成都美女音乐人石嘉佳,还有中国广播艺术团独唱演员林亨,以及抖音的原创音乐人陈焕亮等大咖等各路大咖们,都曾深情演绎过《唱给人民的信》这首歌曲。当时深圳新闻网、深圳卫视、汕头电台、人民视频、学习强国、深圳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广东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中国退役军人网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等百余家媒体,先后都宣传、转发、转播、引用了这首根据诗歌手稿改编创作的“献礼建党100周年”文学歌曲。
可以说,这次诗歌改编成功的传播效果,并非“流行+民谣”的音乐风格形成,而是最初诗歌手稿所起到的关键作用,且作词、作曲和演唱都是诗人易白,这也使得歌曲原汁原味保留了“诗”的本质。而这也是“诗+歌”的创新融合,能在荒芜的诗歌阅读环境中成功“突围”的罕见诗学现象。
我特地对比了《我们终于确诊:集体有“病”——致抗击疫情的转业战友》《公仆之病》及歌词《唱给人民的信》。早期诗歌手稿《我们终于确诊:集体有“病”——致抗击疫情的转业战友》属较为直白的诗歌语言。而发表在歌曲之后的诗歌《公仆之病》,在叙事上则进行了浓缩,反而是“音乐改编版”的歌词《唱给人民的信》经几条叙事线、情绪线等加工处理后,显得更加丰满且浑厚,更能体现出一个时代的历史缩影及社会背景。
总体而言,无论手稿、诗歌或歌词,都保留了诗的本质,也一如既往保留了“容易明白”的诗歌语言风格,至少不会发生令人读不懂的情况,几乎男女老少都能读懂或听懂。
我在一篇题为《人民的声音,引起了争鸣,我位卑言轻,希望有人听》的推文中,认真听了这首歌曲,很多人都留下了评论,这应该就是一种“弦外之音”或共情、共性、共鸣吧。至少我看见评论区,有人评论道:“听完了,只剩下流泪的感动。一样的我们,都是人微言轻。”也有人跟评:“这是一首著名作曲家谷建芬所说的毫无旋律美感的说歌?与唱歌之间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但我认为,易白这种基于“说话状态”与“诗歌朗诵”为基底,略作艺术升华的唱法,听起来更自然,更具有真实感。而这种“真实感”又基于他从前的军旅岁月,在心中所刻下的烙印。血气方刚与雷厉风行等军人特质,形成他这样的“诗歌语言”和“音乐语言”。而民谣的本质是属于大众的,就是描述日常生活和真情实感的。
我认为接地气的诗歌,改编为贴近底层群众的歌曲甚好,能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不会发生“曲高和寡”的现象。而且这样的歌曲听起来,令人感到质朴,走心,真实,不是在“喊口号”或“打鸡血”;同时又有诗的“缘情”和“言志”,并体现了一个时代某个阶段的社会缩影。
最近,广东文联主管,广东音协主办的《岭南音乐》音乐杂志(创刊于1957年),刊登了一篇易白的文章《人民是我心中的天——歌曲〈唱给人民的信〉创作手记》。在这篇回忆创作的自述文中,诗人易白记述道:“出去执行任务时,营里突然通知所有战士写好遗书,放进后留包。当时我随连队作为战略支援部队火速赶往指定地点,战斗了三天三夜。下山的时候,白族的老阿妈和村民们自发组织,送来了热乎乎的盒饭。那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香最暖的饭。部队回撤的时候,成千上万的人民群众在路的两边送别,那一刻我内心笃定地知道——人民,就是我的亲人!”
所以我认为,《唱给人民的信》这首歌不能定性为流行民谣歌曲,当属“音乐诗”或“文学歌曲”,而这首歌创作时能一气呵成,不排除是最初那版诗歌手稿《我们终于确诊:集体有“病”——致抗击疫情的转业战友》刻在了易白心里,所以他抱起吉它创作歌曲时才能灵感爆棚。
回首抗疫三年,曾有一些不了解“本质”和“真相”的“喷子”,就国家当初的“放开”决策,凭个人主观论断在网络上各种抨击,企图阻碍“放开”决策。
可见当时,易白创作发表抗疫诗歌,还是顶了不小的压力。然而,世界上没有永久的苦难,所有的苦难都只是暂时的,疫情在“上下一心”的国人眼中,终究还是低下头了。在疫情防控“放开”前期,易白改稿发表《公仆之病》这首诗,就遭到一些“喷子”吐槽,其实诗人只是个退役军人,并不在体制内,他并不是在为体制内的人说话,更不是在唱什么赞歌,而是基于一个老兵的情怀写了这首诗。
该诗借景叙事,借事论理,由浅入深。通过个体对一座城市抗击疫情的见证,再到对这座城市中一个平凡个体的刻画,以点代面,以小见大。通过质朴的语言和情绪诚恳叙述,犹如微小说讲述抗疫期间发生在都市底层“小人物”身上的小故事,以及内心写照、精神面貌与思想状态等;诗歌标题《公仆之病》的“病”字,更是一字道破了一个集体的共性,那是每个真正的“人民公仆”忧国忧民的共同“心病”;其实这首看似语言直白的诗歌,兼具“记史”和“言志”属性。总体来说,这首诗描述了诗人在深圳抗疫期间所感受的疲惫,以及在疫情困扰中,“人民公仆”对家人的愧疚与牵挂,对群众的关切和忧虑,描绘了“人民公仆”为守住一方安宁,而众志成城,团结一致抗疫的决心。
而他早期诗歌手稿《我们终于确诊:集体有“病”——致抗击疫情的转业战友》,则真实记述了2020年2月期间,诗人独自一人留在深圳过年时,恰逢疫情在各地迅速爆发。而被广喻为“移民城市”的深圳,据说每逢春节期间,就会变成一座“空城”。加上当时严峻而紧张的疫情防控形势,给予了诗人极大的心灵冲击和深层思考。
经常加班加点,落下了一身病,工作稍有不慎就容易引起人民群众的误解,春节无法团聚,思念与牵挂父母、妻子、儿女等共性,是诗人和战友的沟通默契。在诗中,诗人笔锋一转,从刻画“小公仆”转为抒发内心退伍不褪色,退伍不退志的军人本色。也许诗人经常思考着——能为人民群众做点什么?而这一点,似乎成为了“心病”。诗人自嘲自己有“病”,战友告诉他这种念头,其实源于一个退役军人不忘初心和牢记使命的英雄主义。
无论是诗歌手稿,还是诗歌《公仆之病》,或是歌曲《唱给人民的信》,这组作品都客观反映了诗人当时的主观感受及“群体记忆”。而时间也证明了当时疫情防控“放开”决策是对的。回首抗疫三年,那是愁云惨淡的三年,如今成了“过去式”,成了群体的记忆。然而,我从侧面解读易白的创作,在一首描写“个体状态”的都市题材诗歌《大运地铁记忆》又找到了一些线索。
这首诗讲述了底层“小人物”在深圳乘坐地铁的经历和感受,从背起行囊到深圳,到望着空荡荡的地铁思考人生,再到公司倒闭后,乘坐地铁见证了深圳的变迁与发展,诗中的“小人物”也经历了疫情和失业的挫折,但又仍然在坚持写作并记下这些诗行。从个体角度记述了城市的变迁与发展,以及疫情对人们生活的影响;表达了诗人对深圳的热爱,以及对未来的美好期盼。
《大运地铁记忆》这首诗,借鉴了“微小说”的叙事笔法,在诗中展现情景与情节,以个体视角描绘发生在“地铁内”和“地铁外”,以及地铁停运前后的生活变化和思想变化。而诗中故事的发生背景就是深圳,诗中对突然失业的转折处理,也是令人感慨颇多;反观当下社会,又何尝不是很多人失业呢?该诗难免令人联想起诸多在大城市打拼的上班族,以及当代青年所背负的责任,所承受的生存压力。整首诗的叙述非常有节奏且押韵,通过画面感极强的诗行,在叙述与抒情的交叉推进中娓娓道来,而一班又一班的地铁,亦如城中一群又一群“深漂”,因疫情而突然停运的地铁,亦如突然停工、失业的“深漂”。该诗通过“一列地铁”所承载的“城市记忆”将“乘客青春”串联在一起,更将生存危机给“带”了出来,是一首具有“都市特征”的微小说体诗歌。但作为一个写诗多年的诗人及曾经的刊物主编,我更关注促成诗歌创作的生活经历及人生阅历,那才是一个诗人下笔前真正的修炼。
后来读了《离开部队的日子》这首诗,我又发现了一些新的线索。这首诗表达了诗人对军营的怀念,对岁月的追忆;读诗时不难联想到——诗人翻阅日记,在耳熟能详的军营民谣歌声中感到孤寂,于是记下该诗怀念军旅青春和朝夕相处的战友;也许是脱下军装回归社会后,产生了各种不适;也许是在某个深夜,诗人独自审视镜子里的自己,慢慢抬起手敬礼。在诗中,当诗人看见抽屉里的日记本和老照片时,实则在一层一层剥开内心对火热军营的不舍,更刻画了诗人和战友亲如兄弟,又难以割舍的革命友谊。
也许是对岁月的惦念,也许是为了便于演唱及听众理解,在音乐诗歌《那些兄弟》中,诗人大胆采用了典型的“军营民谣”歌词笔法,语言非常直白和朴实,其实这种技术处理不代表没“深度”和“故事”。诗歌虽然未经过多艺术加工,却采用极具“民谣特质”的音乐语言,达成节奏和音韵的自然与和谐,字里行间的情感已然真挚流露,蕴含了诗人扎实的生活沉淀与深刻感悟。诗中既有热血男儿的豪情万丈,也有军营青春的种种难忘,应属接地气的“写实主义”民谣音乐诗。
在探索“诗+歌”的创作实践方面,易白在创作上做过诸多尝试。比如,他11年前唱作发行的个人单曲《小河淌水的故乡》,也是他作词、作曲和演唱,歌词原稿也是一首诗。这首诗浑然天成,诗歌语言尽显行云流水之象。诗人以自己的视角,将青春岁月隐喻为一去不复返的流淌之河。而该诗创作地点弥渡,正是“小河淌水的故乡”。可见诗人触景生情,信手拈来,以景喻情,托物咏志。在诗中流淌之河犹如青春岁月,诗人仿佛化身为天上的云儿,流水又如一面镜子,诗人在镜子中窥见了岁月的无奈,亦如诗人对光阴如流水的惋惜和感怀。值得关注的是,诗中“一看、二望、三叹、四笑、五更、六弦、七绝”等炼字,形象生动的“叠”出了诗人对“第二故乡”的留恋,以及对“第一故乡”的思念,如同岁月中“记忆碎片”在诗人的梦中重叠。
动笔写这篇文章时,我跟诗人通了电话。他给我推送了一些歌曲播放链接,我也细品了一下。也许,是他不满足于诗歌朗诵的传播诗的表达。10年前,诗人还将诗歌和摇滚进行了一次融合,当时在祖国首都的胡同里,在一个传承故事的老牌录音棚里,他将诗歌《灵魂问答》一字不改,直接录制成“轻摇滚”歌曲。毫无疑问,这首歌的作词、作曲和演唱,依然还是诗人易白;据说当时为歌曲演奏吉他的大师,就是跟许巍搭档多年的资深音乐人李延亮。我听后认为,《灵魂问答》也属典型的“摇滚音乐诗”,这首诗简短有力又个性张扬地宣告了“年轻一代”的叛逆与冲劲,写出了青春的憧憬,无论“读”或“听”都足以令人心潮澎湃。
在当时喧嚣的一线大城市,在灵魂浮躁的“群体特征”相互作用下;在经历情感挫折与人生磨难时,诗人采用“象征手法”将心中理想隐喻为“生命之塔”用力攀爬,读来是励志的,也是具有力量感的,且注重音乐的节奏性和律动性;全诗上下前后的“因果关系”和“对比关系”等技术处理都很用心;短小而精悍的小诗耐人寻味;谱曲演唱后更是赋予了诗歌第二次生命;令我想起了四川传媒学院的大学生找诗人拍摄的纪录片。在纪录片中,作为潮语歌曲《潮汕》唱作人的易白;在谈及将诗歌、方言、音乐进行融合的那组镜头里;他一个人坐在一处天台上,望着都市上空的蓝天和白云,手握纸笔说道:“起初,我很喜欢写诗,然后我觉得现在好像纸质媒体不如以前,读诗的人变少了,我觉得诗歌呢,应该需要一条新的出路,我觉得音乐是可以给文学,给诗歌插上翅膀的。”
他的创作感受,令我印象深刻。不可否认,当今时代在进步,传播方式也在改变,诗歌需要探索更多“新”的出路。他这种“诗+歌”的跨界融合创作与表达,本就是诗歌该有的样子,他大部分作品都体现出对“生存状态”的关注与思考,而“与命运抗争”这一关乎人类生存的选题,则是诗人们孜孜不倦,一直在创作的“永恒命题”。
2023年9月,草就于贵州

【作者简介】
蒋德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诗刊》《星星》《绿风》《诗歌月刊》《山花》《鸭绿江》《福建文学》《散文选刊》等近百家报刊发过作品。有诗歌作品被《中国新诗排行榜》《中国诗歌年选》《中国散文诗年选》等39个重要选本选入。已出版文集六部:诗集《水果与刀》《落叶为花》《水落禅生》《青花成色》,散文集《缘来缘去》、《水西听雨》。其中诗集《落叶为花》获第三届贵州乌江文学奖,首届贵州诗歌节尹珍杯优秀创作奖,《水落禅生》荣获第二届贵州诗歌节尹珍杯创作奖。诗歌作品有英、日等语种推介国外。
联系电话:020-81368256 粤ICP备19066410号-1 联系邮箱 : nsj168@yeah.net 联系地址:广州市越秀区人民北路871号
版权所有:广州新世纪艺术研究院
